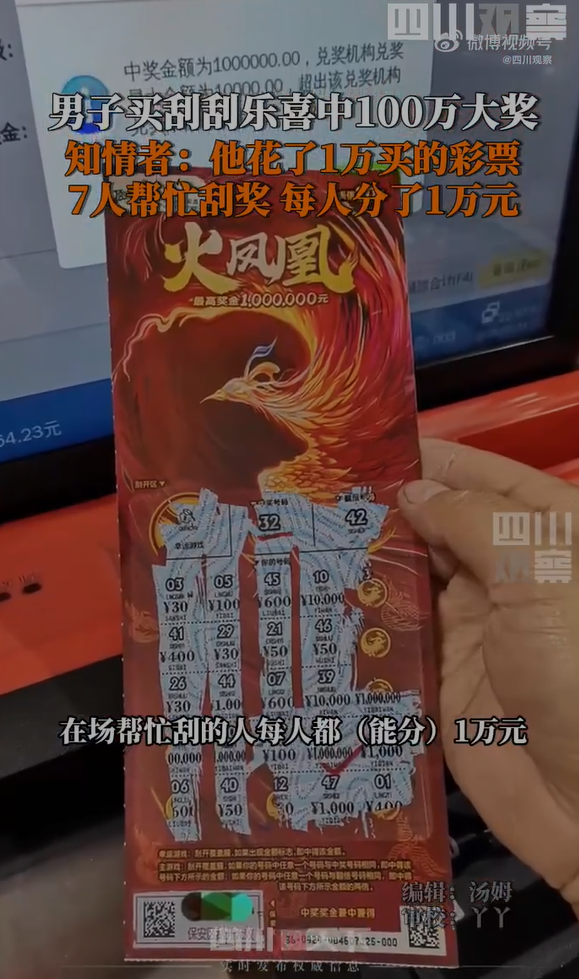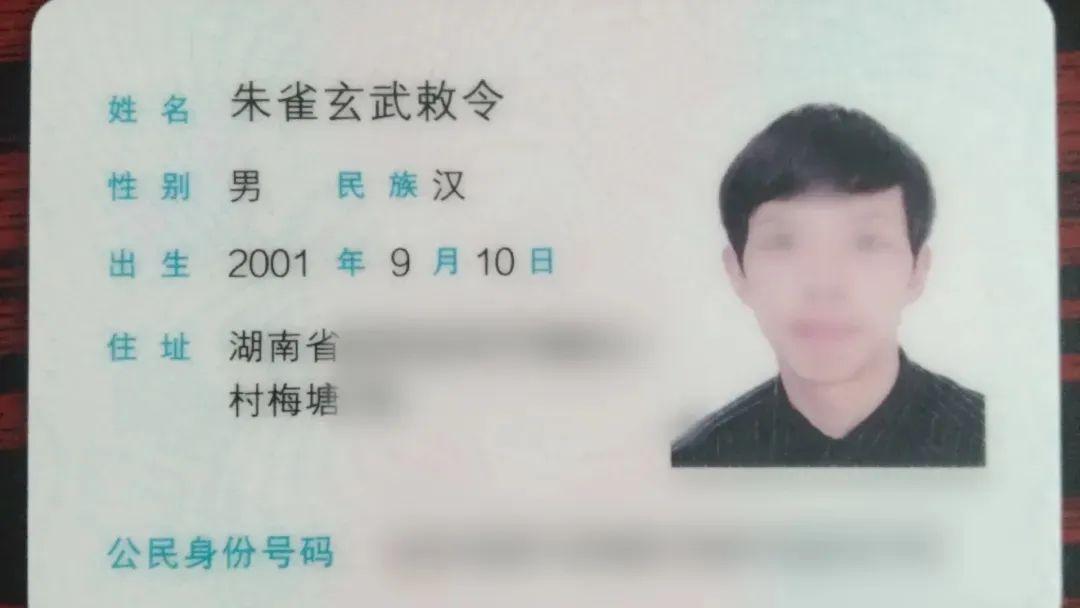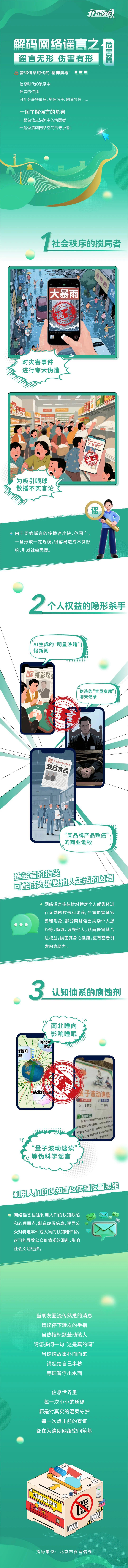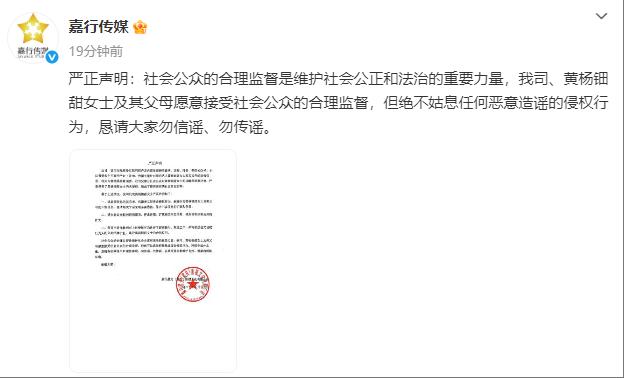再见桃花源|沈颢
 摘要:
CPF | 卡西尼号拍摄的土卫六湖泊很久以前,旧世纪最后一年,我就听说了深山里的这个地方。当时,它被当地政府接管,并有了一个正式的可以印在地图上的名字。而在此这...
摘要:
CPF | 卡西尼号拍摄的土卫六湖泊很久以前,旧世纪最后一年,我就听说了深山里的这个地方。当时,它被当地政府接管,并有了一个正式的可以印在地图上的名字。而在此这... CPF | 卡西尼号拍摄的土卫六湖泊
很久以前,旧世纪最后一年,我就听说了深山里的这个地方。
当时,它被当地政府接管,并有了一个正式的可以印在地图上的名字。而在此这前,它已经以各种绰号、独自存在了四十年。
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朋友,当时称它为,“一个像桃花源的地方”。
这位朋友很好,是纯真年代结下的友谊,一位优秀的记者,软弱而尖锐。对朋友软弱,对坏人尖锐。
而当时,我丢了原先以为能做一辈子的工作,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,正在幼稚地徬徨着。我在昆明遇到这位朋友,他带我去了异常简陋的家,还见到了他的父亲,老人家还用朴素而深刻的语言安慰我。让我印象深刻。
这世上确实存在着,让弱者逃离的地方。当时我想,但并没有生起要去看看的念头。感觉,观看苦难也是一种亵渎。
大概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,忽然就有一天,我发现自己站在了这个村子,但是,它像路上见到的野樱一样,正在凋零。
这是一个自发形成的麻风村,最早起源于五十年代,躲避屠杀的麻风病人逃往深山,建立了它。
而就在十天前,最后一位得过病的老人搬离,村子已经成为空壳,逐步沦为废墟。
最终,这些泥墙的屋子会倒塌,分崩离析,回到大地,仿佛不曾存在过。但在此之前,它们还会像纪念碑一样地挺立一段时间。陪伴它们的,是深山旷古的风,以及永远在此游荡的灵魂。
身体虽然残缺,但灵魂完整。
山里的夕阳时分来得更早,此时落日正在坠向山脊,有一种转瞬即逝的压迫感。一半的山谷已经陷入阴影中。
我在山谷的苞谷地里,上下左右行走,一边回头观察光线与地形的关系。
我在物色一个位置,用于拍摄,它既要在一团温暖的光里,也要能看见那最后一座尚带着余温的完整的泥屋,那位老人撤离后留下的。
老人姓杨,固守在此有半个世纪,村里的其他人要么离世,要么搬走,唯他独守,只因他的母亲就葬在泥屋的后山上。
我刚才其实在后山上走了一圈,荒草丛中有两条交叉着盘旋而上的小径,因为没人打理,两边的灌木正在合拢。不过,我看到了几窝拾级而上的蜂箱,并在蜂箱边站了一会儿,想等着蜜蜂回巢,但除了层出不穷的幽深的鸟鸣,以及谷底下风的回响,没有蜜蜂的痕迹。
老人离开时留下了一只狗,和四只猫,为的是给他母亲的坟墓守灵。附近有租了这片苞谷地的人,时不时会给它们带些吃的。
之前,我们刚从公路下到谷底,靠近村口时,那条狗就开始吠叫,让我们明确了要找的屋子的方位。我们循着吠声走去,直到看到它。
它站在泥屋的入口,泥屋被紫色三角梅、以及白色李子花围绕着,陶醉在暖色的阳光里,确实,像极了桃花源里的原始景象。
狗开始不肯让路,但见我们并不怕它,也可能嗅到了并无恶意,就转到了后山。有几只猫,还没等我们看清楚,就已经跳进荒草中了。
泥屋的位置极好,背山面谷,屋前一片开阔的坡地。坡地上各种花树盛开,其中确实也有不少的桃树,一小块一小块不规则的梯田,随着地形蜿蜒。
田地里一片狼藉,到处是干枯的苞谷叶,经过一个冬天的风雪摧残,正在溶入泥土。这是粗放式手工农作留下的痕迹,散发出难以言说的亲近感。
屋子有两间房,锁着门,有一个门廊。门廊前,屋檐垂直的地上,长着两棵深绿色的高脚油菜,其中一棵正开着黄色的花。老人刚离开这儿十多天,所以,这两棵油菜应该之前就长出来了。
屋前的泥场很窄,只够两个人并排站立,但对于一个独居老人,这已足够宽敞了。在三角梅形成的篱笆下,有一个石盘,里面种着一株兰花,正开着嫩黄的花朵,几乎每个走过的人,都要弯下腰,凑近鼻子嗅一嗅它。
我在前面坡地上找到一个位置,它比屋子的地基低,不远不近的距离。站在那儿,背景里正好有所需要的一切,是整个山谷的最佳位置。
那儿原先也是一小块苞谷地,看上去可能抛荒了。之前在收割苞谷杆的时候,砍刀斜着向下,所以留下了尖锐的根茬儿,像是土地上长出的匕首。我用厚厚的鞋底,把残留的根茬踢裂踩歪。要不,一会儿歌手不小心跌倒,后果难以想像。
歌手是我的朋友保罗,此时,他正坐在屋檐下的廊沿上,弹着吉它练歌。后山的狗还在条件反射式吠叫,在山谷里泛起回音,听上去像是在给歌声打着节拍。
踩完根茬儿,感觉非常解压。再次回头看歌声传来的泥屋,此时,由于阳光的折射,有一个巨大的光晕包围着它,梦幻一般。我忽然想起,多年前那位昆明的朋友说的“桃花源”,指的难道不就是这里、就是这样的时刻吗?
而我,又为何站在这里呢。在那瞬间,脑海里涌现几个场景,似乎都与此有关。
那位软弱双尖锐的朋友,已经英年早逝了。我记不清是哪年哪月,因为那段时间我失去了自由,也没有送别的机会。
在重获自由的那一天,朋友们来看我,告诉了这个消息。当时我有点懵,没来得及去想这件事,朋友们也没有就此展开。因为久别重逢,朋友们争着说话,他们想说的话太多了。
但这种遗憾,像木桩一样地打在了自己脑海深处。现在,我站在这儿,这“桃花源”的废墟上,能算是一种岁月残忍的祭奠吗?
但是,我来到这里纯粹出于偶然,或者说,是一次必然的节外生枝。甚至脑海里的记忆,也是如此。
就在两天前,在炼铁乡的一个旅馆里,我招集大伙儿碰头开会。两位社工,一位义工,三位摄影师,两位歌手,再加上我,一共九人。
我们组成小团队,去麻风村做音乐会。简单地说,去深山里的麻风村,给老人家们唱歌。我给这个活动取了个名字:群山回唱。
在此之前,已经去了两站,老人们都非常开心,后面还有两站。原计划当天休息,因为正好是在中转途中的小镇上。
小镇在罗平山与西山之间,坝子里的一处平缓的坡地上,一派乡野气息。炼铁这个名字,来源于黑惠江上的一座铁桥,铁桥据说是清末杜文秀起义后修建的。炼铁并不产铁,听说最近发现了金矿,所以,在街边面馆里,时不时会碰到一些奇怪的人,在悄悄讨论这件事,很像是某个西部片的开场。
不过,炼铁这两字,听上去倒很像是摇滚乐队的名字。
早上天蒙蒙亮,我爬上旅馆屋顶,想看看日出,顺便回想一下两年前在罗平山徒步的情景。徒步的那晚我们住在深山里的纸厂村,一个海拔三千四百多米高的彝族村落,似乎离这里并不远。
在屋顶上看了太久的月亮,太阳仍没升起,我就已经困得不行了,不得不回房间补觉。
补觉时,我做了一个短暂的梦。梦见又回到午夜的屋顶上,山影依稀,有人朝着圆月唱歌,巨大的霓虹灯在黑暗中闪着坚硬的光,染红了半张脸,但我看不清那是谁。
醒来的时候,我就觉得,既然在这小镇上停留休息,何不就加一场音乐会呢。就在夜晚的旅馆屋顶上。
屋顶上其实很乱,粗糙的水泥地板上,到处裸露着长短不一的钢筯,以及半截水泥柱,意味着这幢楼处于未完成状态,还想往上盖。两个巨大的圆柱形的不锈钢密封桶,大概是供应整个旅馆热水的蓄水池,但看上去像是临时停泊、等待修理的宇宙飞船。
屋顶上四分之一的地方加盖了简易棚子,里面晾满了白色床单。当然,最引人注目临街的旅馆招牌,猩红色的霓虹灯大得惊人,尤其是“炼铁”两字,视觉上非常有冲击力,像是外星人的联络暗号。
就在“炼铁”这两个字背后,在裸露钢筯的包围中,有一小方块空地,正好适合两位歌手搭建舞台。而听众呢,只能坐在那刺向天空的钢筯丛中,像无依之地的鸟。
唯一遗憾的是,歌手所在乐队的名字不是“炼铁”,而是“真途”。但也有点异曲同工。
中午,我召集大伙儿开会,就是商量这件事情。但没有说起早上的梦。
我建议把这场小镇屋顶音乐会,献给长年服务麻风病康复者的社工与志愿者。加上当天下午还要赶来的一位,听众一共四位。
大伙儿都挺高兴,尤其是当晚将成为听众的人。在之后的闲聊中,社工梅子和海菲无意中说起一件事,说不久前,她们回访了一个麻风村,只剩一位老人,但那个村子非常美,像是世外桃源。
然后海菲把回访时航拍的视频发到了群里,大家都惊呆了。摄影师们都急着问,是哪里。
梅子说就在洱海边的深山里,原来人迹罕至,但现在有一条水泥路从附近经过,开车加徒步,三个小时左右可以到达。
梅子大学毕业后就加入了公益机构,定向服务麻风病康复者,已将近二十年,对深山里的麻风村、甚至大部分康复者的基本状况,了如指掌。
她说,这个村子起源于五十年代初期,最早是由躲避集体屠杀的麻风病人、逃入深山老林后建立,慢慢吸引了更多被社会遗弃、又不甘于被命运摆弄的麻风病人,聚集于此。
他们开垦荒山、耕种粮食,自力更生、养活自己。逐渐形成了一个自由而孤立的村落,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,最多的时候有五十多人。
九十年代末,这个村落才有了行政归属,并有了正式的名字。
随着老人们的死亡、搬离,以及下一代因为外出打工,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,纷纷迁移之后,村子开始衰落,现在只剩一位姓杨的老人。
我一边看着视频,一边听着,总觉得这段历史听上去似曾相识,仿佛与记忆之海中某个尚未浮出水面的事物有什么隐约的关系,这是为什么呢。
当然,那时只是偶然从水底冒起了几个水泡,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最后,我问她这个村子叫什么名字。
“玉洱,玉树临风的玉,洱海的洱。”她答。
“哦,那我们最后再加一场吧,就唱给这唯一的老人听。”
还没等我开口,保罗抢先做了提议。
没想到,我提前见到了这位姓杨的老人。
但并不是在计划两天后要去的玉洱村,而是在山石屏麻风村。当天下午,我们去那儿看场地,准备第二天音乐会。
在山石屏大院,我见到了两年前认识的另一位社工阿婵,她来自广东,常年在这一带的麻风村里服务。她当时正在跟一位老人说话。
那位老人脸部与手部有明显的残疾,说话时很兴奋,声音响亮。这时梅子走过来,很惊讶地问他,什么时候搬来的。他说,十天前。
梅子介绍,这位就是中午开会时说起的、玉洱村的最后一位麻风病人。之前她在协调,让身体条件已不允许单独生活的他,搬到条件较好的山石屏麻风村。没想到在李医生的支持下,提前实现了。梅子显得特别高兴。
李医生是山石屏的负责人,也是著名的治疗麻风病的医生,在他的努力下,这一带的麻风病康复者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。前年我们见过面,我的妻子花花十五年前就认识了他。
既是意外,又很合理。第二天晚上,音乐会结束之后,李医生请我们在麻风村食堂简单地宵夜,当我问起玉洱村的事,李医生开心地说,“玉洱”这个名字,当初就是他取的。
“玉”代表美好,“洱”代表深山外的洱海,也代表美好,他挺为这个名字自豪的。后来我查资料时发现,在那附近的山里,原来还真有个玉石厂。
李医生在手机上转了几篇文章给我,居然是九十年代末,他兼职当地新闻通讯员,为媒体写的稿子。
其中有一篇,就是在一九九九年,玉洱村正式命名、以及回归当地政府管理的事情。文中还提到,在八十年代,当地医疗部门其实已经深度介入,到一九九二年,所有麻风病人全部治愈。
这些二十五年前的文字,再次勾起了我脑海中的某些沉睡的事物,并往前推了一把。总觉得互不相关的一些事情之间,冥冥中有着说不清的联系。
宵夜结束后,我跟保罗说,即使玉洱村已空无一人,即将成为废墟,我们还是去唱一场吧,为这段历史,为那些永不磨灭的苦难,以及飘荡的亡灵。
所以,当我终于站在玉洱村的苞谷地里,回望那即将消亡的温暖的泥屋时,那些沉睡的事物,忽然连成了一条线。
我想起了那位早逝的朋友,二十五年前,他告诉过我一个“桃花源”。或许,他那信息的源头,就是来自于李医生的报道。
下午,我们在山石屏麻风村看完场地后,决定把第二天傍晚的音乐会,放在原来卫生院的小院子里。那儿现在是麻风村博物馆的一部分,有很多这几十年留存下来的东西,两位歌手一进到院子,就感染上了一种情绪,说知道明天该怎么唱了。
然后,我们准备去黑惠江边转一转,据说有一处很美的河滩。
黑惠江是澜沧江最长的一条支流,流域面积也最大。起源于丽江玉龙雪山,一路向南穿越崇山峻岭,穿过西山的一段从山石屏麻风村前经过。正是这条河流,与群山一起,让山石坪独居一隅,曾经与世隔绝。
雨季时,山上的雨水大部分排向江里,由于河道高差比较大,河水桀骜不驯,有过几次突发的大洪水,给山石屏麻风村带来死亡与灾难。在这样的河流面前,人只能退让。
河岸边的小路上,正好走来一位老人,他背着一个超大的篓筐,感觉是这个背篓在推着他走。
这也是一位姓杨的老人,之前在大院里见到过,他看上去比较有活力,身上没有明显的因麻风病留下的伤痕。
梅子说,她认识他已有二十多年,这位老人非常热心,乐于照顾其他行动能力比较差的老人。他热衷于种植蔬菜、瓜果,并分享给别人。
和他相依为命的,本来还有一个儿子。但是多年前,儿子因为口角之争,在村子里失手杀了人,目前在服刑。
想起老人还喜欢种树,就问,能否带我们去看看那些树。老人很高兴地接受了,把背篓放在路边,带我们走进了河滩。
这是一处河水拐弯处的河滩,看得出来,湍急的河水容易冲垮泥岸。现在还好,到雨季,情况可能会比较严重。
十多年来,老人一直在此种树,一共种了三四百棵,形成了一片树林。其中以柳树为主,有些树已经很高了。柳树容易活,扎根也比较深,对河岸起到保护作用。
在容易被水冲垮的地方,他还用柳条架框,填上泥土。梅子介绍,他还用自己的补贴积蓄,请来挖掘机,不仅挖出种树的深坑,还疏通堰塞的河道。看得出来,他在这里花了不少心血,种树是为了治水。
见到我们喜欢这片树林,老人咧着嘴,像孩子一样地开心,露出没剩几颗的牙。他还在树林中引了一条小渠,挖了捕鱼的陷阱。
我跟保罗说,要不,就在这儿,唱首歌给他听吧。
保罗正有此意,他拉过斜背着的吉它,弹了几下,然后问老人想听什么歌。
老人一看,开始激动起来,有些手足无措。但是,他还是把我们带到最靠近河水的地方,也可能是他平日里最喜欢的位置,他背对着河水,坐在柳条围起的土堆上。
然后非常庄严地,并拢双腿,并且伸展双手,整齐地放在膝盖上,像一个马上就要进入上课状态的学生,轻声地说:
“可以了。”
柳林里树荫婆娑,江水近在眼前,那流动的水声似乎不是通过耳朵、而是通过眼睛来传递。江对岸的荒滩上,有一株巨大的梨树,灿烂地盛开着白色的花,远看还以为是一群白色鹦鹉。
在下游不远的江面上,静立着一座废弃的铁索桥,在它隔壁,有一座新修的可通车辆的水泥桥,公路已经直通麻风村的大院。
可能再也没有人记起,在山石屏麻风村历史上,那些因洪水引发的灾难了。但是,这位在此生活了四十多年的老人,一定还记得,那些被吞噬的生命。
“
花儿为什么这么鲜
为什么这么鲜
哎,它鲜得使人
鲜得使人不忍离去
它是用了
青春的血液来浇灌
”
我感觉是第一次听保罗唱这首老歌,也许可能只是唱法不一样了。
吉它的枣红色面板上,流动着水面般忧愁的光,他非常平静地唱着,但嗓音里含着一丝颤抖。那颤抖并不是来自唱歌的技法,而是一种自然的共鸣,仿佛像偶尔在风中翻滚的鸟。
有一些光斑落在老人脸上。他庄重的脸,忽然又微笑起来,慢慢又像一个孩子似地咧开了嘴。
他认真放在膝盖上的展开的手掌,也忽然抬了起来,并且抓成了一个半握的拳头,好像拳头里握住了什么东西似的,那东西如此重要,他不舍得放下。
他用两个半握的拳头鼓了鼓掌,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鼓掌的方法。然后他跟着节奏,用那双种下了这片树木的手,打起了拍子。
他非常用力,有一刻他仰起头,手往上挥的时候,重心不稳,身子自然往后一倒,差点就翻进了带着漩涡的江水里。
那一刻,我本能地想伸手把他拉住,但又止住了手。心想,如果他真的掉进水里,就让他落水一次吧,然后再把他拉上来。或许,那更让人刻骨铭心,让日积月累的内心感受,得到一次释放。
音乐正在进入尾声,他应该也能感觉到。此时,在那张衰老得沟壑纵横的脸上,眼泪夺眶而出,但他仍然勉强地笑着。
眼泪越来越多,仿佛不受控制似的。他忽然难为情起来,等吉它声一结束,就匆匆鞠了个躬,口里说着谢谢,赶紧走出树林,背上那个巨大的篓筐,先我们而去了。
他是去找一个地方平复心情,还是让眼泪彻底流光呢。
第二天,我再次一早就醒来了。惊讶地发现窗外一片浓雾,这不就是我们一直想要的吗。
前一晚的屋顶天台音乐会很顺利。在晚霞的映照下开始,仿佛群山也是听众,在月亮与霓虹的结合中收场,仿佛夜色拉上了闭幕。
一结束,就开始下起了雨,雨忽大忽小,一直持续到午夜之后。今早的雾,就是昨晚落下的雨水又回到空气中的魔术。
晨雾中看到梅子她们,开着车出门了,应该是去往鱼贩子那里。今早她们一定要买到两条大鲤鱼,而且一定得是活的。这是上午要拿给廖哥的礼物。
按计划,下午落日之前,我们在山石屏麻风村的音乐会才会开始。而上午,我们先爬上山石屏后山的山顶,去廖哥那儿,名义上也是做一场更自由更简单的音乐会。但是我想,更可能的后果就是,大家在山上玩着玩着,就不想下山了。
廖哥也是属于山石屏麻风村的康复者,但他独来独往,不住在村子里,二十多年前就搬到了后山顶上。山顶上有一小片这几十年来开垦出来的田地,村里其他人因为年纪原因,都爬不上去了。
廖哥六十多岁,身体很好,带着廖嫂在此种植养殖,自给自足,难得下山一次。这段时间廖嫂不在,去外地带孙子了。
廖哥虽然生活简朴,但是个生活家,对食物特别有要求。他说要给我们准备一餐饭,我们问捎点什么上山,他说其它什么东西都看不上,只要我们带两条新鲜的大鲤鱼,而且,不能让鲤鱼在路上死掉,一定得活的。
我们把车开进山石屏停车场,然后借了几个小背篓。每人一个,把吉它、小心翼翼包好的鱼,以及其它物件装进背篓,背着往山上走。本来还想扛一个大音箱上山的,但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,最后决定,在山里还是用自然音响吧,谁让我们这次活动就叫“群山回唱”呢。
前年那次上山是夏天,没有风,酷热难耐。今年正逢最好的春季,山里很美,到处都有盛开的花树,边走边看,目不暇接。只是小路上到处都是枯叶,有点打滑,所以又得专心看路。
我有点想念山顶那棵分叉的大桃树了,前年,花花坐在树下,因感动而流泪。但是这一年内来了六次的小兵说,那棵桃树只剩一半,另外半边,在去年夏天,因虫蛀而倒下了。
接近山顶,一片花团锦簇,所有的果树,都用鲜花在欢迎我们,而廖哥的狗,名叫四眼,用响彻天际的狂吠,警告我们。我对保罗说,至少你的歌声要压过四眼。
廖哥首先把包好的鱼打开,还活着,然后放进了盛满泉水的盆里,先养着。他说,等所有都准备好了,在鱼下锅前十分钟内,才能杀鱼。
每年,廖哥会把自产的李子,腌成酸果浆。今天,他要用这酸果浆,做一道拿手的酸鱼。
除了鱼,其它都是廖哥自产的。
刚坐下没多久,保罗就开始流口水了,他看到了隔壁屋檐下挂着的一排腊土猪肉了。其他人也一样,大家轮流爬上梯子去观赏,贡献一颗吃货之心。
廖哥还宰了一只自家养的鸡。摘好了地里种的菜,那是一种微微带点苦味的甜菜。
廖哥也不让人帮忙,所以,大家就乘机在山顶的田园里闲逛,呈现出散养的状态。此时,往远处眺望,可以看到周边的群山之巅,包括正对面的罗平山。
罗平山正被白色的云雾带缭绕着,像是戴上了一条正在不规则飘动着的哈达。往山下俯视,炼铁坝子上的村落,若隐若现。人间似远非远,似近不近。
小兵说,按这个天气情况,如果是今早日出时分上到山顶,就可以看见整片的云海了。那时候,周边只露出一些山尖,感觉自己像个盘踞山尖的仙人,特别孤独。他去年体会过这种飘飘欲仙的感觉。
前年那次下山之后,我们建议小兵可以在此隐居一年。所以,小兵时不时地从大理开车过来,上山住上一段时间,和廖哥一起农耕、虚度时光,同时梳理一下自己的心田。
小兵带着参观了平时上来后住的地方,那是一间农作物仓库,就是那个外墙挂着腊肉的房子。也是夯土的墙,屋樑很高,里面干净整洁。保罗说,他也想在这儿住上几日。山中一日,世上一年。
小兵一年内上来了六次,他记录了在山上的日常。有文字,也有影像,风格在随意中有股硬劲儿。他也喜欢并擅长自然写作。
在大家的催促下,最近他把文字部分整理成了一本书的初稿。我在来云南的火车上认真拜读了,从硬朗板扎又深情款款的语言中,感受到了他这一年的变化。这将是一部耐读的好作品,非常期待。
乘着廖哥里里外外地忙着,在用来当成客厅的棚子下,围着火塘,保罗与乐队的另一位吉它歌手傅钧,随意地拨弄着吉它,唱起了歌。
大伙儿也是随心所欲,在松树下,在菜园里,在鸡舍,在厨房,在溪水边,在无花果树下,无论走到哪儿,只要在山顶的这片田园里,都能隐隐约约听到他们的歌声。
感觉这才是真正的音乐会,献给群山与田园,而人类,只是寄附其中的微小一部分。
大概四十年前,黄草坝。
如果前面没有写上一个更具体的地名,谁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。叫黄草坝的地方太多,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风烈草黄、荒芜人烟。
这个黄草坝位于凤仪、宾川、祥云三县交界的帽山深处,是一座麻风村,始建于五十年代末。村子靠山吃山,与世隔绝,仅有一条狭窄的小路,穿越漫长的峡谷,与外界相连。
所以,仅在地图上,是找不到这个地方的。即使最近的村子,离这里都很遥远,外人也对此地唯恐避之不及。
就是这样一个隔离了一百多位麻风病人的地方,在那年的某一天,突然冒出了一个陌生人。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,是徒步穿越漫长的峡谷,还是翻越了对面连绵的群山?
他看上去很落魄,三十来岁,身上没有一丝麻风病的症状,完全是个健康人。除了医生和家属,平时这里几乎没有健康人到来。
如果是医生,大家都认识。如果是家属,一般马上就传开了,村子太小了,房子又互相挨着,谁家来了人,就是最大的喜事。
但没有人知道他是谁。
他不仅来了,而且看上去也不愿意走了。他在村子附近找地方落下了脚,似乎对麻风病人没有丝毫的嫌弃。
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来自哪里,他也从来不说,也没有人知道他是专门来此地的,还是偶尔路过。但村子里的麻风病人接纳了他,也没有多问什么,觉得他和村里其他人一样,是个被遗弃的伤心人。
任何人都有活下来的权利。天无绝人之路。麻风病人最懂得这个道理。
他沉默寡言,但愿意干活。山里荒地多,一个健康人,只要肯干,养活自己不是问题。更何况,他也愿意帮助别人。
慢慢地,他与村里一个女人好上了,她是一位姓赵的麻风病康复者。他们住到了一起,结伴生活。
就这样,不管是岁月蹉跎,还是岁月静好,四十年过去了。
村子还是远离人间,村里的人也越来越少,死的死,走的走,由最多时候的一百三十多人,减到了只剩十几个。只是,从最早住的低矮的土坯屋,搬到了政府盖的水泥平房里。
再也没有人记得他是个外乡人了,再也没有人记得他并不属于麻风病康复者。人过七十,他也已老了,老伴也早已去世了。
他依然一个人生活,自己养活自己。看来就这样等待生命的终结。
但命运由天不由人。在生、老与死之间,还有一个病字。衰老意味着接踵而至的病。他病了,不得不被送进医院。
但是他一穷二白,没有钱治病。这时大家才发现,村子里其它麻风病康复者享受的生活补贴,以及医疗救助,他一概没有。
有好心人汇报给上级部门,希望他能得到哪怕一点点的援助。
但民政部门查不到这个人,没有任何有关他的资料,好像他是个凭空出来的人。于是报给了公安部门,请求查询。
最后的结果是,在二零二三年下半年的某一天,可能是第一次,警车开进了黄草坝麻风村。
警车带走了他。原因是什么,没人完全听清楚,大概是他要被遣返原籍,接受审判,因为他是通辑名单上的人。
仍然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来自哪里,他的真实名字。只知道他是个四川人,他不会再回来了。
也没有人知道,这样的结果,对他来说,是否也算是遂了无法说出口的心愿,终于叶落归根了呢。
梅子跟我说起两年前的这件事时,正是在黄草坝麻风村,李奶奶的小屋里。
屋子很小,是李奶奶的厨房,有一个土灶。李奶奶正在土灶后用柴火烧开水。听说我们要在她这儿包饺子给全村人吃,她特别高兴。很少有外来人愿意这么做。上午我们刚到时,还看到她拿着一个捕鼠笼子,里面有一只老鼠。
厨房里没有电,灶火映红了她苍老的脸。等天色开始暗下来的时候,她又拿出了两支蜡烛给我,我点上后放在窗台上。
正是在这烛光里,我们团队中的几位,围着一张低矮的小桌子,包着饺子,饺子皮与馅都是昨夜在祥云县城买好的。
我们包好一批,就先煮一批,然后给村里的老人们挨个送去。黄草坝麻风村不像罗贤观麻风村,没有公共食堂,每个老人自己煮饭吃,而每个人的饭点又都不太一样。
今天白天天气还挺好,有一阵子阳光普照,但到了下午,这深山里立刻就降温了。现在是傍晚,外面还刮起了风,就更冷了。
与此同时,在村里的公共水泥场上,两位歌手,保罗与傅钧,正在搭建今晚演出的舞台音响。他们把吉普车直接开到水泥场上,停在一棵桃树与一棵李子树的中间,然后拉出装在车顶的露营卷篷,篷下就是舞台了。
在天色还没完全暗下来之前,可以看到,车后那两棵大树上,分别开满了粉色与雪白的花,正是它们一年中最美的时候。
因为冷,就点了一堆篝火在舞台前面。篝火在夜风中飘忽不定,取暖效果有限。在黄草坝后山山顶上,有一排巨大的风力发电机,在夜色中,像魔鬼的刀刃一般,在转动中发出惊恐的回响。
站在观众位置往前看,篝火、舞台、若隐若现的花树、花树下房子的暗影、远山山脊上的月光、以及直逼天顶的风力发电机,正好在同一个画面里。一会儿歌手弹起吉它唱起歌,就有种超现实的恍惚感。
我送煮好的饺子给歌手时,他俩已经开始练歌了。
公共水泥场周围被一圈老旧的土坯房包围着,有一半人去房空,处于半坍塌状态。在水泥场的入口处,也有一棵开满花的李子树,路过的人,只要往上一举,就能触摸到浓密的香味。
有一位戴着助听器的老人,双手插进裤兜,站在树后面的夜色里,靠近屋檐下的一堵泥墙。我招呼他去吃饺子,但他专心看着练歌的歌手,一动不动,似乎不想和任何人说话。
回到厨房,说起这位老人,在烛光下,海菲一边继续包饺子,一边说起了他的故事。
老人是大理古城附近的村民,得麻风病时候,已经有一对儿女,但是还很小。
那是七十年代,他不得不离婚,儿女自然跟随了母亲。他被迫离家,来到这苦寒之地黄草坝,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
三十年过去了,他没有一天不想念孩子。终于有一天,因为太煎熬了,他托人联系到了他们,约好了在大理古城南门见面。他等了一天,但是始终没有孩子的踪影,当然,也有可能他完全认不出他们了。
他很失望,但是他不得不离开那儿,因为当地的旅店不接待麻风病人,而且他也没有住旅店的钱。
他坐上最后一班公交车,回到离黄草坝最近的镇上。那晚下起了暴雨,电闪雷鸣,他在路上拣了一块塑料布,披在身上,时不时在闪电照耀下,凭着记忆穿越峡谷,走了二十公里山路,回到了黄草坝。
没过多久,村子里来了大学生志愿者,梅子当时就是其中一员。
老人又燃起了希望,托志愿者去老家找儿女。志愿者按照他说的地址,来到了大理古城三塔附近的村子里。她们问一位正好路过的当地妇女,并且说明了情况。
没想到对方一口拒绝,并且责问她们为什么要帮助麻风病人,火气特别大。
她们觉得莫名其妙,继续往前走。没想到,那位妇女走了一段后,又回头追上来,哭着说:
“他是不是要死了。”
志愿者赶紧说明,他没有死,只是太想念孩子了。这时,这位妇女抹掉眼泪,再次怒斥:
“如果真的为儿女好,就不要打扰我们了。我们都有自己的家庭与生活。”
原来,这位路人恰好就是他的前妻。
志愿者只好放弃了。后来再次回到黄草坝时,才知道,那天晚上,他的一对儿女,可能以为父亲真的快要死了,只想见最后一面,于是当夜就骑着三轮车,经过漫漫长途,骑到了黄草坝。
不知道那次见面最后发生了什么,那的确可能就是最后一面了。又是二十年过去了,老人真的变老了,记忆也在丧失,但是人依然还在,只是从来没有回过一次家,儿女再也没有来过。
麻风村里也不尽是苦难。
其实当天一早,汽车穿过峡谷里拓宽的土路,在悬崖上蜿蜒前行时,我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错觉。
面前这片连绵的群山里,一共隐藏着三个麻风村,分属于相邻的三个县。以前,它们各自被当地驱逐,实行严格的隔离,但是它们之间却有着联系,通过深山里那些神秘莫测的小路。
我称之为“苦路”。去年,在罗贤观麻风村的志愿活动结束后,我与小兵去探访过其中一条。本想从罗贤观一路走到黄草坝,但找路花了太多时间,当年的一些小路,因为太久没有人经过,早就湮灭了。最后我们只走了四分之三的路程,没有到达终点。
所以,这次既然到了黄草坝,就想着从相反方向,继续走上一小段“苦路”。
我还想起,去年徒步启程前,罗贤观麻风村的老人都叮嘱我,一定要看看“龙潭”,这一路上最美好的地方。
他们的叮嘱让我充满了好奇。尤其是那位姓罗的老人,他就是这条“苦路”的获益者,就是通过这条隐秘的路,他年轻时走到了黄草坝,并且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。
这条路见证了两位麻风病人的爱情,这样的案例可能不少。而龙潭,从老人们说起这两个字时双眼发光的样子,让我猜想,除了沟通友谊,那儿可能就是约会、缠绵、以及依依惜别的地方。
早上,当车子接近黄草坝的时候,我从峡谷的高处,越过成片的芳草往下看,其实有一丝的惊呆。这个本以为风烈草黄的无依之地,在温暖的晨光下,在群山与花树包围之中,居然一派世外桃源的感觉。
尤其是村子周边,成片的红土地,被整理得一丝不苟,可以想像曾经有多少残缺的手,在上面劳作过,以换取活下来的可能。
在村口和老人聊了一会儿,问起是否记得罗贤观麻风村罗爷爷的老伴,她们都还记得,只是听说两年前去世了。
她们还说起,两年前,村里有位失忆失智的老人失踪了,搜寻了几天几夜,都找不到。最后,她还是被牧羊人无意中发现的,在一个山洞里奄奄一息,而这个山洞,居然就在通往罗贤观的其中一个峡谷里。是什么隐秘的记忆把她带去了那里?
梅子提醒说,如果要去龙潭得趁早,因为来回还要十公里的山路,路并不好走。
如果不是下午还要和村里老人一起包饺子,我们可能会在龙潭停留更久。
它是崎岖山谷里的一小块平地,有一处泉眼,周边挖出了一个圆形水潭,潭壁用石头加水泥砌成。
从规模看,以前泉水并不小,因为还修了一条水渠,把水引到下边树林。它曾经是生命力的象征,只是现在它干涸了,水潭中间竖着几块长了青苔的石头,石头上系上了红布。这是对龙王的祭祀吧。
龙潭边有一棵分杈的大树,只剩下大半截,看不出是死是活,但是为它砌了一个水泥台,可以爬上树叉。仔细看,它也有着龙的形状。保罗与傅钧就爬上去唱了一首歌。
离树不远,有一处奇怪的石窝,从侧面看,石头的形状像是微型的火山口,从高处看,是一整块不规则的中空的石头,中间长出了一小块草地,形状有点像是希腊字母中的欧米茄。
我忽然觉得它更像一个神圣的器官形状,是人类繁殖力的象征。于是让一位义工缱缩着,以胎儿的形状,侧躺在里面,果然,天衣无缝,它更像是一个母性的子宫。
石窝内的地面有着微妙的弧度,正好符合人体的背部曲线。石窝内的大小正好够两个人紧紧相拥而卧。所以,或许,它更适合做一张爱的婚床。
不知为啥,我脑海中浮现出了哈代小说《德伯家的苔丝》中的最后场景,那个石头阵,在现实中也真实存在。
那是个古老的史前遗址,象征着献祭。那是苔丝宿命的终点,她疲惫地问一起逃亡的安吉尔:
“
这些石头
是不是
古代异教徒的
神坛
”
上天赋予了苔丝超凡的美貌,却附带了无穷尽的苦难,像是无法摆脱的诅咒。一切都该结束了,她更愿意把血洒向异教徒的神坛,用精神的背叛表达最后的反抗,并在自我献祭中获得救赎。
这些石头赋予了苔丝一种奇异的安慰。她在祭坛上面躺了一夜,直到黎明时分,警察包围了石头阵。这位世上最纯洁的女人,平静地接受了即将来临的死亡,她说:
“我准备好了。”
在离开龙潭前,我让保罗与傅钧坐进石窝,弹着吉它唱了一首歌。那场景,也很像是坐进了一艘石头的刚朵拉小船。
他们唱的,是两天前在罗贤观麻风村时,保罗为这条二十公里长的苦路写的歌:
“
直到你为我开放,直到你为我悲伤
这二十公里路啊,如此的漫长
我们的青春啊,早已悄悄流走
”
我想起很多年以前,保罗还在某地当记者,我约过他写了一篇调查报道,导致他在当地无法容身,于是我就把他召唤到了广州,并肩工作。
那时,我们都把职业使命当成了自己的桃花源。包括那位逝去的朋友。
现在,我们各自剥离。他成了一个歌手,而我差不多成了一个流浪者。命运,不再如以往理解并期待的那样,是一条莫比乌斯环,而是由无数冰块与卫星碎片构成的土星之环。
土星照命,我们还会找到与未来新的联结吗?
作者:访客本文地址:https://ddwi.cn/ddwi/11367.html发布于 2025-05-16 15:26:12
文章转载或复制请以超链接形式并注明出处爱美网